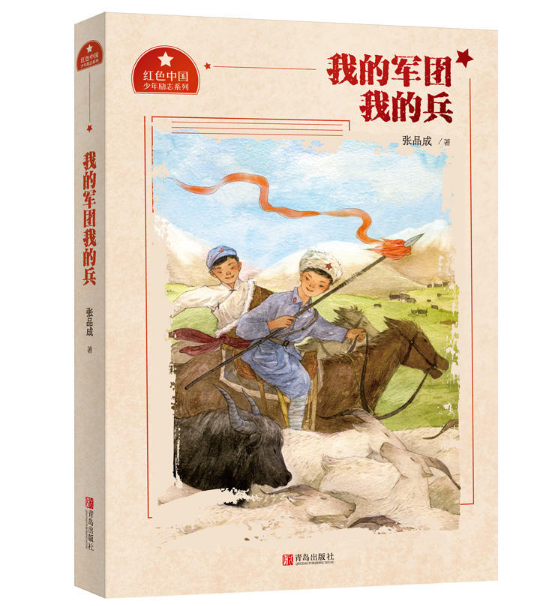
《我的軍團我的兵》張品成 著 青島出版社出版
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張品成從事文學創作以來,他始終將紅軍生活作為小說創作的主要題材。他特別著力于為青少年讀者創作“少年紅軍”如何在戰爭中成長的小說。例如:中短篇小說集《赤色小子》《永遠的哨兵》《九天》,長篇小說《覺醒》《紅藥》等。
在當下英雄主義被放逐的消費時代,張品成的長篇小說《我的軍團我的兵》選擇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這條道路通向兒童戰爭小說敘事的內在性,展示了兒童文學紅色書寫的另一種可能。
然而,張品成對戰爭兒童小說敘事的內在性探索,談何容易!姑且不說張品成要從他以往的“紅軍小說”的敘事中突圍出來,單說“紅軍小說”敘事在二十一世紀背景下的內外交困就具有十足的挑戰性。為什么這樣說?其一,從“紅軍小說”創作的歷史傳統來說,紅軍小說歸屬于革命歷史小說家族,雖然已經確立了主流歷史敘事觀念,已問世了《閃閃的紅星》《萬山紅遍》《找紅軍》《云崖初暖》等紅軍小說名作,但總體說來,紅軍小說在中國當代小說史上尚處于革命歷史小說家族這個當代文學高地上的低洼地帶。因此,如何繼承革命歷史敘事傳統并探索新的歷史敘事方式,這應是張品成在創作《我的軍團我的兵》時所要面對的一個難題。再從“紅軍小說”創作的現實語境來看,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新歷史主義思潮的大面積影響和市場化因素的全面開花,使得包括紅軍題材在內的革命歷史敘事傳統或被文壇邊緣化,或被大眾文化市場娛樂化。中國兒童文學創作同樣難以幸免:銷量PK質量,歷史上的“少年紅軍”等小英雄形象被遺忘。如何讓紅軍題材小說成為今日中國兒童成長的精神資源,這應是張品成在創作《我的軍團我的兵》時所要面對的另一個難題。或許,正是基于這樣的創作難題,張品成在《我的軍團我的兵》中,左沖右突、迂回前進、探索新路。僅以敘事層面來說,他時而續寫紅軍故事,時而重寫紅軍故事;時而主張崇高美學,時而插入詼諧美學;時而表現兒童的單純性,時而表現人性的矛盾性。經由種種努力,《我的軍團我的兵》實現了兒童戰爭小說敘事的內在性。
那么,張品成在《我的軍團我的兵》中如何實現兒童戰爭小說敘事的內在性?概言之,張品成既以敬畏紅色歷史之心自覺繼承了紅軍的精神傳統,又以文學的形式對紅軍歷史故事進行個人化重述。
在《我的軍團我的兵》中,張品成非但并未如時下新歷史潮流或大眾文化市場那樣顛覆或戲說革命歷史小說的敘事傳統,而是更為自覺地承繼了革命歷史小說的敘事傳統。這一點集中體現在這部長篇小說中的如下三個特質:對英雄主義主題思想的選取、對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對崇高美學的追求。不過,張品成顯然不是一味地繼承革命歷史小說的敘事傳統,而是試圖在二十一世紀的歷史語境下對其進行新解。因此,這部長篇雖然意在講述紅軍的長征故事,不可避免地縈繞著死傷氣息,但它打動讀者心弦且極具震撼力的則是今日世界上嚴重喪失的東西——莊嚴、大愛、友誼。特別是這部長篇小說意在以繼承革命歷史敘事的方式提醒今日人們,特別是提醒今日兒童一定無比珍惜那些已被視為習以為常的東西——飽食、安居、生命、和平,進而以文學的形式應對今日兒童精神“缺鈣”的現象,并助力于塑造兒童堅硬的骨骼、頑強的性格、大愛的心靈。
在《我的軍團我的兵》中,張品成對革命歷史敘事傳統的自覺繼承與新解并不必然獲得意義的內在性,因為意義只有內在化于敘事世界,意義的內在性才會得以實現。這樣一來,戰爭故事別致的講述方式、莊諧雜糅的敘述語調、飽滿的“少年紅軍”形象的塑造、少年心理的成長過程和戰爭本性之間的內在關系,一并構成了這部長篇小說的戰爭敘事的內在性。
在故事講述方式上,這部長篇一如既往地選取少年視角來講述紅軍的革命歷史故事。但在少年視角下,以往革命歷史小說中重點渲染的正面戰場的殘酷死傷情景被放置在小說背后,借用小說的敘述者所說:“樊天九和歐前響他們是普通士兵,當然不知道問題的嚴重性。”(《我的軍團我的兵》第35頁。以下的引文注釋將這部小說名字略去。)事實上,這部長篇小說的開篇一句——“過了瀘定橋,交火的事就少了”——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它的戰爭敘事的“非戰爭性”。即便這部小說不得不描寫戰爭的死傷,也是以或隱蔽或節制的方式進行側面描寫。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整個小說緊緊圍繞少年主人公樊天九在戰爭中的所見所感來展開情節。這些情節符合少年的單純心理,傳遞了少年獨有的童真童趣。這樣的情節隨處可見:樊天九參加紅軍的目的是“有飯吃有衣穿,不挨餓受凍就行了”(第8頁);樊天九和另一位少年歐前響幸運地發現了一壇酒,卻沒有料到戰士因饑餓而將“咂酒”變成了醉酒;為了保障前線戰士的生命安全,樊天九偷偷試吃野菜,轉危為安后,卻說“夢見了仙人指路哩”(第82頁);樊天九在接受了看放牛馬羊這一特殊任務后,“很快就喜歡上了那些牛馬羊”(第161頁),還給它們取了名字,并將它們看作“隊伍”和“軍團”,等等。
與講述方式密切相關的是敘述語調。如果讀者足夠細心,還會發現這部長篇小說中的莊諧雜糅的敘事語調,由此確證了張品成的兒童戰爭小說的獨特敘事美學。“莊”意指作家在這部長篇小說中講述正面事物時的莊嚴語調,即對革命歷史敘事傳統的一種歷史性接受;“諧”意指作家在這部長篇小說中講述中間事物時的詼諧語調,即對革命歷史敘事傳統的一種現實性新解。例如,小說先以莊嚴的語調讓少年主人公樊天九信誓旦旦地想:“英雄要有英雄的樣子,為工農犧牲,是值得的,名垂千古。”(第99頁)隨即又以詼諧的語調寫道:“天九想說,但做不到。他知道身上的陣陣劇痛讓他的眼不像眼,鼻子不像鼻子,嘴不像嘴。”(第99頁)“莊諧”之間的距離不到幾秒鐘的時間。再如,小說以莊嚴的語調講述了營長史統有的“顏面不能丟”的生命尊嚴和不怕犧牲的精神,同時又以詼諧的語調講述了他的孩子氣和對死亡的忌諱心理。英雄氣與孩子氣奇妙地存在于史統有這位紅軍營長的內心世界中。其實,不止是這兩處心理描寫,還有更多的描寫表明:這部長篇小說的總體敘述語調表現為寓莊于諧。如果說莊嚴的語調是對革命歷史小說中的崇高美學的回歸,那么詼諧的語調則是對革命歷史小說中的觀念的新解。
當然,不管講述方式多么富有新意,敘述語調如何特別,兒童戰爭小說的成功敘事都不能缺失對飽滿的少年人物形象的塑造。回望以往講述“少年紅軍”的成長故事的革命歷史小說,不難發現,“少年紅軍”形象常常被單面化,仿佛生來就是一個因苦難而負有某種神圣使命的、意志非凡的英雄形象。而在《我的軍團我的兵》中,少年主人公樊天九雖然生來就攜帶一部父母雙亡的苦難史,但這部長篇小說非但未重復以往革命歷史小說的復仇史,反而似乎隱去了這一復仇史,而始終將樊天九當作一位成長中的少年來對待。于是,樊天九自成為“少年紅軍”后,始終保有了少年形象的豐富性:既有紅軍戰士的精神氣質,也有天下少年的兒童天性,還有這個少年本身的個性特征。而且,在這部長篇小說中,樊天九不是一個人在成長,而是被適時地“配備”了另一位同伴——性格迥異的少年歐前響,與其形成既對照、又互補的關系。與此同時,這部長篇小說還打破了少年的專職導師制,為樊天九設計了成長路途上的不同出身、不同身份的精神導師們。他們是:給予樊天九溫暖和關愛的秀英姐;教導樊天九懂得尊嚴和服從命令的史營長;教導樊天九辨識野草和大局的封院長。盡管上述精神導師的背后都有一個黨的光輝形象,但無不是有弱點的肉身化的人。
這部長篇小說如果只是將“少年紅軍”的塑造放置于紅軍的“后方”,而不呈現戰爭的本性對兒童的身心傷害,就不能說有根本性的突破。其實,兒童戰爭小說敘事的內在性最終取決于能否在戰爭本性中塑造人物形象。所以,在這部長篇小說中,除了上述文學性探索,張品成將“少年紅軍”的成長心理與戰爭本性結合起來,進而塑造出處于變化中的“少年紅軍”的成長心理,這一點,特別令人叫絕。為了體味紅軍長征的艱難險阻而多次重走長征路的張品成認為,戰爭“不僅有肉體的傷亡,還有常人不可能經歷的精神磨難。那些經歷,比死亡還要痛苦。”(張品成:《寫在前面的話》)所以,《我的軍團我的兵》的特別之處并不在于深描看得見的戰火,以及講述戰爭如何帶給肉體生命疼痛和傷亡,而在于呈現那些看不見的心理煎熬,以及表現戰爭如何帶給“少年紅軍”的生命考驗和精神磨難。特別是,這部長篇小說重點講述兒童成長的心路歷程。這樣,如果說這部長篇小說的前半部分主要將兒童性和紅軍的精神傳統融合在一起,那么它的后半部分則將戰爭的本性和兒童的人性相結合而帶出這部小說的高潮。其中,第八章以后故事懸念的設計使得“少年紅軍”樊天九的心理波動一浪高過一浪:樊天九看管的由牛馬羊組成的“我們的軍團”不斷“減員”,“少年紅軍”的心理愈加起伏不定,謎底終于大白——原來是被首長派人借走了,樊天九心如刀絞……紅軍的精神傳統猶在,但戰爭的本性必須正視。
這部長篇小說產生了“少年紅軍”和紅軍的精神傳統以及戰爭本性纏繞在一起的神奇、微妙和變化莫測的景象——這種景象構成了這部長篇小說的獨特的兒童戰爭敘事的內在性,也使兒童文學紅色書寫實現了另一種可能。
作者:徐妍




請輸入驗證碼